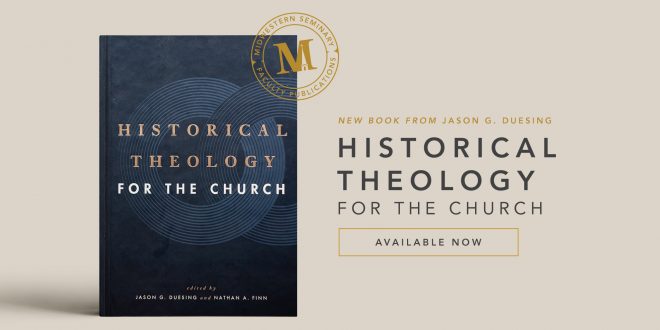文/詹森·迪辛(Jason G. Duesing) 译/穆桑 校/无声
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太13:52)
引言
大卫·莱文(David Levin)着手记述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早年生活(1663–1703)时,称其为“主的纪事官”(the Lord’s Remembrancer)。[2]这一称号取自英国历史悠久的司法职位——王室纪事官(King’s Remembrancer)。这一文书职位设立于十二世纪,提醒王室勿忘过去被记录的事务。不过鉴于马瑟在塞勒姆(Salem)审巫案[3]中所扮演的角色,授予他这一荣誉称号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马瑟生平的这一页往往掩盖了他作为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与圣经注释家所撰写的杰出作品。他的巨著《基督在美利坚的奇妙作为》(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是他杰作中的典范,也是莱文赋予他“主的纪事官”这一称号的主要原因。马瑟的历史类著作忠于事实,旨在为新英格兰提供一部教会史,莱文因此对他大加赞赏。他指出,马瑟“作为历史学家的力量来自于他所举范例的范围与数量,以及他所述主题的恒久存续——数十个真实人物的敬虔、信心、挣扎、困惑与顺从”。[4]
历史神学家的身份是教会的仆人,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提醒当下与未来的读者,使他们想起教会历史上早期的行动与神学发展。作为“主的纪事官”和忠实的历史神学家,他们应该能够服事当下的教会与未来的教会,但是具备怎样的前提才能做到这一点?这项工作如何展开?本文将呈现对历史神学的回顾式考察,并提出为教会建构历史神学的愿景。
一、什么是历史神学
在审视过去或思考未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问题——评价历史上的神学是否可行?鲁益师(C. S. Lewis)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得而知的。他坚称,“鲜活的时间中仅仅一秒钟所包含的内容,也是记不胜记的。”鲁益师并不是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不可知的,因为他承认“过去的重要部分存留了下来”。[5]所记录的事情值得了解并加以分析,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过去的真相,从而可以与其他时代进行比较。我们还可以追溯诸多作者在其所处时代与处境中是如何理解各项教义的。
如果研究过去确有价值,过去的真相可以确定下来,形成一个称为“历史”的研究领域,那么,什么是历史神学?从本质上讲,历史神学揭示了历史探究的过程,服务并支持与其本身不同,但可以与其相容的其他学科。要为历史神学下定义,一个有益的进路是将历史神学抽离出来,使之独立于其他学科。首先,历史神学为古典教义提供历史背景,从而补上系统神学与圣经神学的不足。事实也确实如此,历史学家要么遍览圣经,采集经文依据,来完成自己的系统神学架构;要么通过各卷正典,以圣经故事作为面向,来完成自己的圣经神学架构。其次,历史神学提供了一个宝库,里面有对构成基督教历史故事的人物、地点、事件和社会因素的研究,也有对教义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从而补上教会史的不足。教会史回顾神学家的历史;历史神学研究神学家的思想。
要考察历史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还有一种方法,即探讨传统在基督教历史中的作用。正如罗文·威廉斯(Rowan Williams)在其新近修订的《为何研究过去》(Why Study the Past)一书中所作的解释——“教会一直是‘从事保存’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关注过去,关注自己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与上一代人做着相同的事情。”[6]尽管基督徒常常为传统与圣经的关系,或一种传统与另一种传统的关系而辩论,但基督教的历史显明,基督徒有意竭力地与过去保持联系,并且看重其他基督徒是如何在个人生活中、也在共同体中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么,当下与未来的基督徒应当如何理解过去的传统?基督徒又当如何从那些已经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人那里获得帮助或纠正?历史神学记录了历代基督徒的教义发展,记录了他们如何将自己的传统传给下一代,从而为我们提供上述问题的答案。
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指出,历史神学作为一种教育学工具所具有的这项教导作用,对于历史研究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神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基督徒与教会,从那些生活在不同时代、历经试炼而刚强壮胆的人那里获得教导,也可以使他们理解其所继承的。麦格拉斯解释说:“像从前从未有过神学研究一样研究神学,绝无可能。我们总是需要回头去看,去看看事情在过去是怎么做的,当时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样。愿意认真对待自过去而来的神学遗产,是‘传统’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7]
为了描述这一作用,请思考一下,当旁人观察二人对弈时会发生什么。对战的两人已经开启游戏,因此旁观者不得不观察棋盘,评估发生了什么,谁会赢,下一步该谁走,谁占优。旁观者观察着正在进行的游戏,并运用自己对游戏的认识,评估正在实施的策略,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人对游戏了解越多,就能越快地适应这种情况,但无论何人都愿意从一开始就观察游戏,好全面了解比赛。其次,如果对战者能停下来向旁观者解释走了多少步,犯了哪些错,每位棋手当时在想些什么,旁观者会很得益处。如果一位棋手离开棋局,请旁观者接替自己去下,则会产生第三层的趣味与复杂性。这个时候,旁观者要想有机会胜出,就必须具备知识、经验,不仅要知道自己承继了什么,还要明白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
历史神学的研究,情形就是这样。当下的基督徒与未来的基督徒,一旦他们开始基督徒生活之旅,无论是以个体身份,还是以地方教会成员身份,都被置于旁观者的位置。在他们之前的基督徒正在或已经与基督教传统“下了许多盘棋”。每个人都发展出处理圣经教义的技能,也都为“在各个时代与独特环境中,如何过基督徒生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如果旁观者不仅有机会在所在的群体中研究、学习游戏规则(出自对圣经的研究),也有机会向附近与从前时代的其他基督徒学习,并且观察同样的事情他们是如何做的,则必会受益。不仅如此,当旁观者(往往身在地方教会或家人群体当中)被带进一种教会传统,迁至一个新的社区或加入一个新的家人群体时,就会面对接手游戏的要求。经由历史神学研究而形成的门徒训练对旁观者有所辅助,有助于旁观者了解所处的新环境,之前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历史神学是教育学工具,会对即将进入这些景况的基督徒也有所辅助。
谈及历史神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定义,本文引介三个常见定义:耶罗斯拉夫·帕利钦(Jaroslav Pelikan, 1969)将历史神学定义为“对耶稣基督教会基于上帝话语所相信、所教导、所认信之内容的研究 ”[8];麦格拉斯(1998)将历史神学定义为“旨在探索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识别在其形成过程中产生影响之诸般因素的神学研究分支”[9];格雷格·埃利森(Gregg Allison, 2011)将历史神学定义为“对过往教会的圣经阐释与教义建构之研究”。[10]本文也给予初步的、个人原创性定义:历史神学是对出自圣经的基督教教义与传统发展的研究,由教会进行,并且为了教会。
二、回顾: 历史神学的历史
研究历史神学不仅要搞清楚究竟历史神学是什么,还需要考察历史神学的历史,历史学家研究神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已有多长时间,主要的人物都有谁等。
清教徒托马斯·华森(Thomas Watson)在默想“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8:28),和上帝能否以及如何在罪恶的环境行出良善时,想到了圣经中的参孙的故事。他说:“从这头狮子身上竟有蜜出来,真是奇妙。”[11]历史神学在历史上的作为,伴随着人类在每个时代所导致的缺陷与错误,但当我们回顾这一切时,还是会因为发现蜜而惊叹。不过,历史神学也对历史运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斯特拉特福德·考尔德科特(Stratford Caldecott)提醒我们:“人类文化的每一次伟大变革、每一次新生或复兴,都是因为从过去寻回某些有价值的事物而引发,是这一行为使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发展成为可能。”[12]鉴于上一段探讨了历史神学是 “什么”(what),本段旨在介绍历史神学所涉及的“谁”(who)与“如何”(how)。这种回顾性考察,其功用是继续打一层基础,最后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建造,以期当下与未来可以对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有所理解。
1、历史神学家的历史
1986 年,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校友礼拜堂发表了他的教职演讲。在题为“不能被逐出的教义:服事教会的历史神学”(Dogma beyond Anathema: Historical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的演讲中,乔治表示历史神学“在神学体系中是相对较新的学科”。[13]他的意思是,虽然古典的基督教传统自早期教会以来就经历了传承与评估,但直到改教家回归源头开始批判罗马天主教时,历史神学的实践才得以发展。[14] 换一种说法,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当新教教徒试图了解罗马天主教会在历史上错在何处时,重估教会传统的需要才得以萌发。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在阐述教会史和国家史之间的区别时,特别强调了前者的重要性。[15]以此,始于改教运动的历史神学,作为至关重要的工具,帮助每个改教家进行了重建教会的工作。
改教家利用历史神学复兴基督教传统,可是启蒙神学家却利用历史神学来“去基督教传统”,以便进行重塑工作。乔治认为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依照基督徒的自我意识从根本上重新解释了传统教义,从而彻底改变了现代神学”。[16]鲍尔(F. C. Baur,1792–1860)将黑格尔(Georg W. F. Hegel,1770–1831)的逻辑学用于教义发展,因而将大部分基督教传统的价值废掉了。对历史神学的启蒙式进路在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那里达到顶峰。乔治指出,哈纳克的《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本身就是将教会从教义式的基督信仰解放出来的绝佳手段”。[17]乔治的意思是,哈纳克认为《尼西亚信经》与《迦克墩信经》对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败坏了耶稣的朴素教导。因此,在哈纳克看来,历史神学的任务就是去历史,回归朴素真理之内核。不过正如历史所示,这种进路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很像纳尼亚世界中的那段惊险奇遇,尤斯塔斯·斯克鲁布(Eustace Scrubb)企图刮掉自己的鳞片,使自己“去龙化”——当一个人“去基督教传统”,令传统的内核显露时,会发现其实正是鳞片构成了龙。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去龙化,就不再是龙。
启蒙运动之后,也有一些神学家没有遵循哈纳克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在乔治看来,十九世纪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与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af,1819–1893)这两位神学家“强调教义发展的有机性,强调教义扎根于教会更广阔的生活之中。”[18] 到了二十世纪,来自不同基督教传统的几位神学家也从传统视角审视教义发展,撰写了历史神学著作。鲁益师·伯克富(Louis Berkhof,1873–1957)从改革宗传统出发,撰写了《基督教教义史》(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s,1937);雅罗斯拉夫·佩利坎(Jaroslav Pelikan,1923–2006)从路德宗传统出发,撰写了五卷本的《基督教传统》(The Christian Tradition),但其中也包括了对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考察;冈萨雷斯(Justo L. Gonzalez,1937– )以卫理公会神学家的身份撰写了《基督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1970–1974);杰弗里·布罗迈利(Geoffrey Bromiley,1915–2009)从圣公会传统出发,撰写了《历史神学》(Historical Theology,1978)。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 世纪初,几位福音派神学家贡献了几本历史神学著作。圣公会人士麦格拉斯撰写了《历史神学》(Historical Theology,1998,2012);支持阿米念主义的浸信会人士罗杰·奥尔森(Roger E. Olson)撰写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1999);支持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人士埃利森(Gregg R. Allison)撰写了《历史神学》(Historical Theology,2011);圣公会人士杰拉尔德·布雷(Gerald Bray)撰写了《上帝已经发言:基督教神学思想史》(God Has Spok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2014)。
2、历史神学的历史编纂学
这番考察提供了一些见解,大致呈现了改教运动以来历史神学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不过也有人更细致地回顾了教会史与历史神学的编纂学。如何回顾教义在历史中的发展才是恰当?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正如鲁益师笔下的“界中林”(Wood between the Worlds),“里面有几个池塘,是通往不同地方的入口”,有一群学者不仅讨论历史神学是什么,而且讨论发展历史神学的最佳、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完成评估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这项任务,最好跳进哪个池塘?杰伊·格林(Jay Green)的《基督教史编纂学:五种互相冲突的版本》(Christian Historiography:Five Rival Versions)是大有助益的工具,确立并评估了至少五种完成任务的方法。鉴于本文的意图在于,为了服务教会,给历史神学研究大致确立植根于圣经并符合改教家所复兴之基督教传统的方向或倾向,所以对于护理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方法对伦理学与护教学的影响等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须另择时间。在这个时候,本文只想确立一点,即从狮子身上也能得着蜜。历史神学的研究可以为教会服务。
三、前景: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
历史神学的当下与未来前景如何?发展服务于教会的历史神学会是什么样的?本文的结尾,我们要开出清单,列出服务于教会的历史神学都有哪些特征。以下是从显出这些特征的著作中援引的例子,同时也表明未来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这份清单绝不是最终的或全面的。这里的意图是在本文的结尾给出具体蓝图,作为未来继续建构所遵循的纲领。
1、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维护“圣经高于传统与历史”这一立场,但也承认传统与历史的价值
一方面,这一声明意在直接明确一个共识:改教运动以唯独圣经的呼召为核心理念,以此批判与纠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做法,即将传统权威提升到等于甚至高于圣经权威的地步。将圣经视为赋予教会的唯一无误的权威,这一立场是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的起点。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历史神学而言其他至关重要的权威就完全不予考虑。事实上,基督教历史上的信条与信仰告白是在圣经之下的基准,用于确立教义在历史上的发展。不过,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与改教家站在一起,都承认如下事实:唯有圣经是至高无上的,因而圣经之权威,是判断所有其他权威的标准,也是理解与遵循所有其他权威的依据。
另一方面,上述声明认可了圣经与神学学者就“神学释经”(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IS)运动仍在继续对话。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有关“神学释经”的讨论正式出现。此类讨论主要源于一种愿望,即恢复在启蒙运动的历史批判法大行其道之前、与教会历史相连的释经理念。蒂莫西·乔治于1986 年向教学人员致辞时说:“我们求索经文的意思,不仅要问经文在原初背景中是什么意思(旧约与新约研究的特定任务)、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与实践神学的共同任务),还要问纵观基督教经验这庞大的连续统一体,它已经表明了什么意思。”[19]从某些方面看,这番话预见了“神学释经”的关切。关键在于,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究竟如何将这两种意思结合在一起。2011 年,卡森(D. A. Carson)以《神学释经,是的,但是……》(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Yes,But…)一文就神学释经运动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分析。在这篇文字中,他以六个观点总结了讨论情况,阐述了神学释经的支持者在哪里提出了正确问题,并提出了其个人富有洞见的问题。[20]这篇匡谬性论文有助于说明,“神学释经运动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并不是新的”,“神学释经中的新东西,不是含糊不清,就是错误”。[21]神学家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和斯科特·斯温(Scott Swain)与卡森志同道合,启动了《教义学新究》系列丛书(the New Studies in Dogmatics series),旨在依照“藉复兴以更新的规划”来构建神学。也就是说,“与矢志探究基督不可测之丰富的、教会最值得信赖的教师们(古代的、中世纪的与现代的)对话,从而更深地汲取圣经资源”,[22]以这种方式来寻获神学。最近,克雷格·卡特(Craig Carter)的《以伟大传统解释圣经》(Interpreting Scripture with the Great Tradition)一书也努力遵循这一平衡,认为“古代的解读方式在教会中从未完全消亡,相较于现代诠释学提供给我们的方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少主观性、更有规范性地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一事实很有价值。[23]当代的这些向导承认基督教传统对理解与诠释圣经的价值的同时,努力维护圣经作为唯一权威的首要地位,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应该倚重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2、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遵循两条最大诫命,正如它服务大公教会,它也服务地方教会
内森·芬恩(Nathan Finn)的做法极有价值,他依照 “最大诫命”描述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且指出,使基督教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正是动机。一个人研究历史,是否 “从根本上说是为主献上的敬拜”,是否致力于“理解、领会过去的人为什么那样做,即使历史学家不认同那些行为本身”?[24]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致力于研究教义的发展,并以此为爱上帝的举动,爱邻舍的举动。[25]爱上帝,就是爱耶稣基督所爱的教会,祂为教会舍了自己(参弗5:25)。纵观基督教历史,何谓教会这个问题一直是大小争论与分裂的根源。然而要构建历史神学,则必须对何谓教会有简要理解。《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The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381)从四个特征描述教会,认为教会是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教会的大公性或普世性“逐渐作为‘正统’(orthodox)的同义词使用”。[26]托德·比林斯(Todd Billings)的说法极有价值,他将这种意义上的“大公性”描述为 “地下水位”( underground water table),即所有传统在其深处都具有的作为共同基础的整体性。[27]与此类似,鲁益师对传统的描述极为有名:
一个大厅,有几扇门通向几个房间。如果我能将谁带进那个大厅,则于愿已足。但是炉火、椅子与饭菜在房间里,不在大厅里。大厅是等待的地方,是尝试推开各扇门的地方,而非居住的地方。[28]
因此,从某一个层面看,历史上的教会共享一个“大厅”,即表达在各种传统中的根基性的、信仰告白式的共识;离开大厅有“房间”,即众地方教会可以在其中团契与生活,同时与更大的基督教传统保持联结。[29]地方教会需要与更大的教会中的其他传统团契相交,以便在某一个层面领会与发展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东西。
但不仅如此,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教会也需要与大公教会中已不在人世的其他人交流。罗伯特·特雷西·麦肯齐(Robert Tracy McKenzie)指出:“据估计,曾经在世的人类当中,当下仍被注意到的只有6% ,我们却将其他94%的人一笔勾销,将历史从课程中剔除,转而学习所谓更加实用的科目。”[30]从众多例子中列举其二,如果约翰·加尔文没有机会与奥古斯丁交流,我们会如何看待他的神学?如果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没有珍视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的著作,现代宣教运动何以能加速发展?教会重视大公教会在历史上的其他形式与传统,并且向其学习,从而爱上帝,爱邻舍,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才会得到最好的构建。
3、构建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是实现履行大使命、荣耀神这一目的的方式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7 中解释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他的意思是,他和他的读者生活在耶稣再来之前最后的日子里。从那个时代时起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教会一直生活在世界末日的边缘。彼得解释说,虽然教会中的信徒应该将目光与盼望集中于耶稣即将并必然的再来之上,但他们无论是服事的还是讲论的,也应该全然为了荣耀神而使用自己的属灵恩赐。也就是说,无论是吃、喝、传道、培训、浇灌、收割、打字、写作、分享,还是门徒训练,教会都应该为了履行大使命,荣耀神,按圣经规定的方式做这些事,直到末了。简而言之,构建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是为让福音在全球广传而充实与坚固教会,是要看到认识神荣耀的知识遍及万民,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 2:14)。[31]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其功用是作为工具,可以让教会得着装备,去学习并将教义发展史介绍给没有历史神学的人。
4、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作为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与实践神学的朋友而发挥作用时,具有学术特质与建造之功
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作为其他伙伴学科的朋友而非对手发挥功用时,则是大有助益的。朋友的概念对学术工作来说,既是一种隐喻,也是不可少的现实。作为一种隐喻,历史神学之为其他学科的朋友,表现为它填补了历史与圣经和神学分析之间的空白。鉴于系统神学家与圣经神学家可能希望在不考虑历史的情况下构建神学,历史神学家发挥着大有助益的功用,确保其朋友不会偏离基督教传统或教会在历史上的工作太远。同理,从事实践神学或教牧神学的人容易为了适切性或修辞的实用性这一冠冕堂皇的原因而抛弃传统,对他们来说,历史神学家可以大有助益地提醒我们,认识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是具有实用性的(传 1:9)。如此一来,又回到了国际象棋的比喻,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是作为其他学科的朋友来发挥功用的。具体表现为,它常常“将”他们工作的“军”,在他们周围进行三角测量,设法理解他们的每一步动向,并将他们与其他时代的其他系统神学家、圣经神学家与实践神学家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历史神学家作为朋友,正在帮助当下教会的神学家在与过去的教会、未来的教会的联结中继续自己的工作。
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作为这些学科的朋友发挥功用,还体现为互相建造。正如鲁益师所说,信徒之间意义重大的友谊并非出于偶然。“曾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的基督”,也可以实实在在对每一伙基督徒朋友说:“不是你们拣选了彼此,是我为你们彼此拣选了你们。”[32]基督教传统中的各类神学学科也是如此。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受到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与实践神学的挑战与磨砺时,就会得到坚固。当这些学科为了服务教会而比弟兄更亲密时(参箴18:24),就是在以主耶稣为门徒展示并提供的榜样为榜样。祂就是当祂的教会因为罪而与祂分隔、与祂远离时,以自己的血为代价使她靠近自己的那位(参弗 2:12-13)。祂爱教会,舍了自己的生命,称教会为朋友(参约15:13-15)。
5、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开展工作是以教会仆人的身份,而非教会主人的身份
蒂莫西·乔治讲述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神学贡献的,他说自己是 “驮着重要的担子上路的那只驴子的亲属”。就像门徒在耶稣荣入圣城前,蒙耶稣指引找到了那头驴子,说:“主要用它。”(可11:3)同理,巴特认为自己被上帝使用,就是在需要用他时“恰好在场”。他解释说:“我们的时代显然需要一种与当下的神学有些不同的神学,而我得蒙允许,成为驮着更好的神学走了一段路,或者竭力去驮好它的那只驴子”。[33]学术事业是服事主人(主耶稣与祂的教会)的驴子的工作,当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明白这一点时,就对教会大有助益。这只驴子以两种方式工作:
首先,为教会研究历史神学的历史神学家虽然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却也承认在上帝的计划中居于中心的是教会,而非学院,并以此为乐,以此提醒他人。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斯科特·马内奇(Scott Manetsch)最近出版的《加尔文的牧师团》(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收录在“牛津历史神学研究丛书”(the Oxford Studies in Historical Theology series)中。这部著作考察了1536–1609 年间日内瓦牧师的教牧神学,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马内奇在书中指出,他的主要关切 “不是在评判日内瓦牧师时采用某种‘怀疑诠释学’(a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而是在依照加尔文及其同侪所处的独特的历史与宗教处境评价他们的教牧实践时,秉持仁慈与批判性的细致敏锐”。[34]毫无疑问,并非所有针对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的尝试都会直接侧重于教会层面的分析,但马内奇对日内瓦牧师生平的调查,其倾向是正确的,他将学术探索的重点倾向服务教会的方面。纵观历史,神学家与其他教会领袖经常着眼于教会(而非仅仅着眼于学院),发现或呈现来自过去的神学真理,从而坚固他们那个时代的教会。这种类型的历史神学所关注的,是其所指向的所在,所致力于发现的,是于教会而言的善、真、美之事在历史上的超验性发展。[35]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兴以更新”的理念再次为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充当了合适的使命宣言。
其次,历史神学家为了教会研究历史神学,当他们也让教会正视它可能不想看到的教义发展的意义时,就是很好地服务了教会。换句话说,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应该时常揭露过去的教会与当下的教会的盲点、罪恶与不自洽。虽然圣经是完美的,但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却并非如此。历史神学家必须谨慎地提醒教会,站在过去许多有瑕疵的巨人的肩膀之上,同时指出这些巨人的错误与失败。斯特拉福德·考尔德科特在《因真理而美丽》(Beauty for Truth’ s Sake)一书中提到了大巴西尔(Basil the Great,330–79)“跟随蜜蜂”、以在有瑕疵的历史中发现美善的做法。
因为(蜜蜂)既不会一视同仁地趋近所有花朵,事实上也不会试图将它们栖落其上的花朵全部带走,只会从那些花朵中采撷宜于它们工作的部分,其余部分不会触碰。如果我们是智慧的,我们自己也会这样,从这文献中汲取适合我们、近于真相的部分之后,忽略其余部分。就像我们从玫瑰花丛摘取花朵时,要避开刺尖一样,我们从这些著作收集有用的内容时,也要保护自己不为有害的内容伤到。[36]
当下的历史神学家并非每次尝试都没有错误;这就要求其他历史神学家为了教会的缘故去识别那些错误。举例来说,约翰·费亚(John Fea)在他的《为什么要研究历史?》(Why Study History?)一书中提醒我们,许多“向教会介绍美国历史的尝试往往充满了真理与解释上的基本错误,或者这些尝试是用于摆弄过去,以推动当下的宗教或政治议程。”[37]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所发挥的功用就像驴子驮着主)竭力为当下与未来的教会纠正当代对过去的误用时,才是很好地服事了教会。
为教会从事学术研究并非没有代价。罗伯特如此告诫学者:“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所蒙的呼召,很可能会与学术文化的价值观迎面相撞,因为学术文化对就过去所作明显的基督教式反思持怀疑态度,对往往引发我们信仰群体关注的问题不屑一顾,对面向大众读者的学术研究条件反射式地不信任。”[38]虽然如此,为教会从事历史神学研究的历史神学家有幸像驴子为主效劳一样,从事卑微的工作,谨慎地引导教会去发现历史中的善、真、美的事物,同时指出许多学术皇帝实际没穿神学外衣。
这部著作是为我们这一背景中的教会所撰写,因此为这部著作所遴选的作者都坚信《浸信会信仰与信息》(the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2000),这份文件为我们力图服事的教会提供了很好的指引。此外,选出来的作者都具有学术资质来教授这些内容。盼望这部合集式的著作能很好地服事到我们的教会。原定的作者名单中还包括了一些来自不同少数族裔背景的声音,但由于个人或专业上的各种原因,一些作者由于其他事宜无法继续参与。我们相信,神已经引导这一项目需要的声音,使其忠于祂的话语,卓越地服事教会。[39]
结束语:主的纪事官
本杰明·科尔曼(Benjamin Colman)在科特·马瑟下葬后的讲道中指出,马瑟在他的文字作品中大放异彩;他极其善于表达,从他的宝库中带出的新旧宝藏无以计数。由此可见,不仅是他的心灵、意志与情感,他的智慧、想象力、创造力、敏捷的思维与敏锐的洞察力也都归上帝为圣了;他的丰富从他的唇间流溢,就像蜜从蜂窝滴落,喂养所有靠近他的人,就像精炼的银子一样,既华美又明亮,既令人快乐又使人受益。[40]
耶稣教导我们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当历史神学家从历史的众多教义中拿出珍宝,并作为主的纪事官来服事教会时,历史神学的研究就可以用来服务教会。
作者简介:
詹森·迪辛 (Jason Duesing) 担任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教务长、学术管理副院长和历史神学教授。2008 年,他在西南神学院(Southwestern Seminary)获得历史神学和浸信会研究的博士学位。他和他妻子育有四个孩子。
[1] 本文是Historical Theology for the Church一书的“导论”内容,Jason G. Duesing and Nathan Finn, eds., Historical Theology for the Church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21), 11–27。题目为编者所加,内容略有编辑,承蒙授权,特此致谢!——编者注
[2] David Levin, Cotton Mather: The Young Life of the Lord`s Remembrancer, 1663–170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16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人们认为是“巫师”作恶。 随着女巫案情不断扩大,塞勒姆镇(现在的丹佛市)及周边城镇邻里之间的相互指控达到白热化阶段,最终共有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堆压死。——编者注
[4] Levin, Cotton Mather: The Young Life of the Lord`s Remembrancer, 1663–1703, 262.
[5] C. S. Lewis, “Historicism,” in Lewis, Christian Reflecti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7;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4), 132, 134.
[6] Rowan Williams, Why Study the Past?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Church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05, 2014) , 91–92.
[7] Alister E.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1998; Wiley, 2012), 12.
[8] Jaroslav Pelikan,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3.
[9]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9.
[10] Gregg R. Allison, Histor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1), 23.
[11] Thomas Watson, All Things for Good (1663; repr. n. p.: Banner of Truth, 2013), 44.
[12] Stratford Caldecott, Beauty for Truth’s Sake(Grand Rapids: Brazos, 2009), 12.
[13] Timothy George, “Dogma beyond Anathema: Historical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Review & Expositor 4 (Fall 1987):693.
[14]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10–11,认同并且特别指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发现他们必须熟悉教父神学与在中世纪对这些理念的修正”。
[15]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3rd e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66–68.
[16] George, “Dogma,” 697.
[17] George, “Dogma,” 698.
[18] George, “Dogma,” 699.
[19] George, “Dogma,” 701.
[20] D. A. Carson,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Yes, But……” 见于Theological Commentary: Evangelical Perspectives, ed. R. Michael Allen (London: T&T Clark, 2011), 187–207.
[21] Carson, 207.
[22] Michael Allen and Scott Swain, “Introduction to New Studies in Dogmatics,” Common Places, April 16, 2015. https://zondervanacademic.com/blog/common-places-introduction-to-new-studies-in-dogmatics.
[23] Craig A. Carter, Interpreting Scripture with the Great Tradition (Grand Rapids:Baker,2018), x.
[24] Nathan A. Finn, History:A Student’s Guide (Wheaton, IL:Crossway,2016), 21–22.
[25] 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26] Mark Dever, The Church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2) , 18.
[27] J. Todd Billings, “Rediscovering the Catholic-Reformed Tradition for Today, ” 见于Reformed Catholicity, Michael Allen and Scott R. Swain (Grand Rapids: Baker, 2015), 153。
[28] C. 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1952;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xv. 乔治·马斯登指出,这一观点并未被罗马天主教徒接受,原因如有人所言,“罗马天主教定然会坚持认为,所设想的大厅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其他宗派或多或少是附着于它的附属物或附属建筑”。C. S. Lewis’s Mere Christianity: A Biography(New Haven, C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0。
[29] 对这一见解的更多评注,见Jason G. Duesing,“Baptist Contributions 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见于 Baptists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ed. Matthew Y. Emerson, Christopher W. Morgan, and R. Lucas Stamps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20), 329–50.
[30] Robert Tracy McKenzie,The First Thanksgiving: What the Real Story Tells Us about Loving God and Learning from History (Downers Grove, IL: IVP, 2013), 11.
[31] 最初以类似话语对这些思想的探讨,见Jason G. Duesing,“A Denomination Always for the Church: Ecclesiological Distinctives as a Basis for Confessional Cooperation,”The SBC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ason K. Allen rev. ed.(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9), 109–25。
[32] C. S. Lewis, “Friendship,” 见于The Four Love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1960;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7), 114. 引文参考的是HarperCollins 版。
[33] George, “Dogma,” 707.
[34] Scott M. Manetsch,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35] Roger Scruton, Beau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提醒我们想到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超越性,即“万物拥有的实在特性,因为它们是存在的各个方面,是存在的至高恩赐向理解力显明的方式”。
[36] Basil the Great, “To Young Men, ”引用于 Stratford Caldecott,Beauty for Truth’s Sake:On the Re-enchantment of Education(Grand Rapids:Brazos, 2009),16–17。
[37] John Fea,Why Study History?(Grand Rapids:Baker,2013),160.
[38] Robert Tracy McKenzie, “Don’t Forget the Church: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Dimension of Our Dual Calling,”见于Confessing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Historian’s Vocation, ed. John Fea, Jay Green, and Eric Miller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0), 281。
[39] 谨向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与锡达维尔大学(Cedarville University)致谢,感谢他们主持本项目的初期策划会议,并就编辑层面提供有益的建议与鼓励。《服务教会的历史神学》一书得以付梓,部分归功于这份宝贵支持。
[40] Levin, Cotton Mather, ii.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